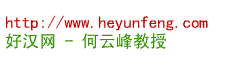|
特别推荐
1. 好汉网主何云峰教授2. 中华学人行为规范195条
3. 中华劳动价值规范
4. 中华公共道德公约
5. 马克思学在线词典
6. 中英文歇后语大全
7. 中华成语大词典
8. 汉英心理学词汇
9. 更多在线辞典
好汉教苑热门话题
1. 高职思想政治课采纳参与式...2.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 民办高校大学生思想特点及...
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
5. 如何教孩子学英语常用词
6. 评教授建议语文课本删除《...
7. 教育法学参考资料目录
8. 小学语文课本写『林阴道』...
9. 对下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10. 近十年留守学前儿童教育问...
何云峰:建立和完善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架构
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既要研究教育伦理的问题又要研究教师道德的问题。而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本质的区别。从教育伦理的角度看,相应的跟教育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是最核心的内容;而从教师道德的角度看,教师的教育行为符合有关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是最核心的内容。在最理想的道德自觉状态下,教师的教育行为能够没有任何外在的律令和监督便能符合有关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此乃最高的道德慎独境界。然而,任何的道德至善主义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已。现实的社会中,教师的道德行为往往不总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教师个体不可能始终如此,教师集体也不可能。因此,在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之间通常需要一个中介环节——那就是教育伦理规范或教师道德规范。规范也就是规则,其理据是相应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其作用是将伦理要求变成可操作的道德律令。笔者以为,除了在规范的意义上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具有相同的意义外,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样的区分对于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具有独特的意义。
(一) 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之间为什么需要行为规范作为中介? 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是所有道德领域的前提。不存在相应的伦理责任和义务,也就没有道德要求的必要,因而也用不着相应的规范/规则。于是,责任/义务规范/规则道德/行为,形成一个必要的链条。在这里,规范/规则是责任/义务和道德/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 之所以需要行为规范作为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是因为: 第一,只有明确的教师行为规范才能将教师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和义务明晰化、可操作化。教育是一个全人类的事业,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政府及其部门、每个公共政策都可能涉及到对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的担当问题。对于教育职业从业者而言,这样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更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不同的个人和单位或部门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教育伦理责任,并不是每个人和单位或部门都完全明确的。大家知道自己有相应的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但对具体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却未必都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中介组织或部门,将应然的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转变成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对于教师群体而言,跟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其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第二,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是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性,而教师的师德状况却在不同的时空里有不同的表现,这需要跟据师德状况适时地调整相应的规范。相比较而言,教师行为规范需要因时因地地加以修订和完善。例如,当前我国就出现师德状况不如人意的现象,这跟整个社会风气不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法制不健全等等诸多因素有关。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需要对相应的教师行为规范进行建立和健全。一旦师德状况发生变化,则相应的教师行为规范又必须及时调整。所以,教师行为规范是应然层面的教育伦理与实然层面的师德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当我们制定师德规范的时候,不能脱离师德实际地试图追求一蹴而就的效果。 第三,人类道德的不完善性必然要求道德律令的约束。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每个教师都是道德完美主义者,以为每个教师都会自觉履行自己应尽的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成为道德“圣人”。当然,也没有理由假设每个教师都是道德上的“恶人”,没有规则,就不能从善。然而,我们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假设,有的(或者少数)教师存在着道德上的不完善性,或者说会(至少有时会)违背教育伦理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因为只要有一个教师如此,这个命题就成立了。不过,由于教师群体中具体哪个人是这样的“道德不完善者”,是无法确知的,所以在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道德不完善者”。于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对这种不确定的道德不完善性进行制度性的规约,要求每个教师都必须遵守,以防止他/她现实地成为那个道德不完善者,从而有限地实现人类的道德至善追求。 经中介组织或部门依据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转化出来的道德规范应该具备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必须跟责任和义务是直接关联的,不能超越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提出另外的要求;第二,必须是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包括具体指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而且必须跟原则性的抽象规定明确区别开来;第三,必须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有明确的处罚条款,甚至可列明细的负面清单;第三,必须符合不同的主体角色特征,不同的道德主体具有不同的伦理责任和义务,相应的道德规范应该跟据不同的角色特点,提出不同的明确要求。总之,具体的道德规范应该具有规约性,是由抽象的教育伦理法则转换而成的具体细则。 总之,没有了具有约束性的教师行为规范,就无法明确各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也无法对教师道德实际状况进行规制,更无法推进人类有道德不完善走向道德至善。中介的存在必要性也就是在于它去厘清这些具体的规则,以达到有效规制的目标。 (二) 谁最适合充当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角色? 既然教育伦理义务与教师道德之间需要行为规范作为中间环节,那就必然会产生谁来制定这种行为规范的问题。考虑到道德本身的特点,这个中介角色充当者(即规则制定者)最好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符合道德本身的非强制性特点;(2)符合道德践行的自觉性(自律性)特点;(3)对教师群体具有规约性。 从可能性的角度看,可以假设这样几个可能的规范主体(规则制定者):(1)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机构);(2)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3)学校;(4)教师(即个体性地自我约束)。 首先,政府部门制定教师行为规范,应该说,是有充分理据的。政府要管教育,当然就要管教师,所以政府制定教师行为规则,完全可以被看成是教师资格标准化和专业化的重要内容。然而,政府制定师德规则有一定的问题:一是违背道德的本性。道德在本质上是非强制性的。而政府制定道德规则就必然具有强制性。这是政府本身的强制性所决定的。在我国,更是如此。政府制定的规则就相当于“行政法”,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刚性的师德规则跟道德的本质本身是不匹配的。二是在双轨制下面,民办教育机构的教师似乎难以很好地包容进去。我们的现行体制是,民办教师不属于“体制内”的教师,属于“企业员工”的性质。这就天然地产生了“合理性”的问题:待遇和社会地位上他们不是教师,在法律规则遵守上却又是教师。这是自相矛盾的社会管理现实。如果考虑到我国当前存在的这两种情况,笔者以为,政府并不是非常恰当的师德规范制定者。 其次,学校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表面上,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学校是教育的主体单位。它当然应该对自己的员工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不过,这里有一定的问题。学校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是可以进行道德上的提倡和规约的,那就是:只要在我学校做教师,你就必须如此。但是,组织文化是学校可以抓也可以不抓的,学校可以把它看得很重也可以不看重它。因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它即使不明确制定教师道德规则,也完全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中心任务。这样,如果制定教师行为规范的责任完全交给学校去承担,就会在不同学校之间呈现巨大的差异。而这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教师道德发展的,对于教师履行相应的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具有诸多弊端。某些管理松懈的学校,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师德问题。 其三,通过教师自我约束,以完全依赖于教师自觉的方式,提升教师道德建设,这虽然满足了道德的自律性要求,但无法保证教师群体的道德自觉性。如前所述,人类道德的非至善性是始终存在的。完全依赖教师的自觉性去实现教育伦理义务的担当,既不符合人类道德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教师道德的发展。 最后,这样,只有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教师道德规则的制定者,才是最恰当的。换言之,笔者以为,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担当教育伦理和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角色,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行业中介既能降低政府规章那种过于刚性的强制程度,也能体现教师自律性特点。对于教师个体而言,行业中介具有外部约束的特征,但从教师群体整体看,行业中介仍然属于教师的自我约束,即以集体自律要求个体自律。行业中介也可以消除学校间的差异性,防止对师德建设的态度冷热不均现象出现。 总之,教育从业者行会作为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组织,去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是最为合适的。 (三) 从强化行为规范的制定和执行角度,反思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治理架构 虽然教育从业者行会具有担当中介角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我们国家也面临着中介组织不健全、政府不愿意转变职能等问题。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组织不发达,社会中介组织更是不健全。有人呼吁:应该加强行业协会的作用,成立专门的教师行业协会,使之成为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作为教师职业准入和水平认定的权威机构,弱化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而且有的学校的确也成立了老教授协会、女教授协会、青年教师协会等类似的内部社团,个别的社团还偶尔具有一定的跨校特征。然而,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行业协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伦理与教师道德之间的中介角色往往只能由政府来担当。于是,政府出台的各种教师道德规范,就不断涌现出来。而它既不像法律那样严谨且具有威慑性,又不像行规那样具有自律性。政府具有科层性特点,所以在制定此类师德规范的时候,也不得不层层出规则,最后还要指望学校去出细则。结果,师德规范实际上要么重复上级政府的,要么不伦不类。要是建立了相应的教师行业协会,全国制定一个统一的规范,最多各省市再制定一个师德规范,也就行了。政府对教师道德行为的监管因而也就可以主要变成对行业协会的监管。当教师道德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主要应该对教师行业协会施加压力,促使相应的行业协会对师德进行管理和自律。这样,政府主要不是针对教师个体进行监管,而是对行业整体的监管;而行业再对个体进行约束,充当有效的中介角色。这对于避免政府与个体之间的直接冲突,维系政府的威权性,具有很大的帮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个体都是有单位归属的,即使没有单位的个体,也会有居委来管理。于是政府主要跟单位和居委打交道。这是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即“政府—单位+居委—公民”的三位一体结构。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独有的公民社会。所以,笔者认为,中国从来不缺少公民社会,认为公民社会没有发展起来,这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的。从公民社会的建构目的来说,公民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为了提高社会动员和公民力量组合的有效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咱们长期形成的“政府—单位+居委—公民”的三位一体公民社会结构,是非常不错的体制。不过,这个三位一体架构,应该根据不同的治理需要灵活运用,才能使我们的公民社会健康地发展起来。 拿教师道德建设来说,在理论上,“政府规章-学校细则-教师自律”三位一体的框架似乎也不错。但这个框架将道德建设与社会建设混为一体了。在社会建设方面,也就是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政府-学校-教师”构成有效的教育资源体系。但是,教师道德建设的问题,主要是教师的职业道德问题,不属于社会动员和公民力量组合的范畴,所以不能利用“政府-学校-教师”的框架去管理,而必须用“政府-行业协会-教师”的结构去治理。 如此看来,如果要真正使我国的师德建设卓有成效,就必须从抓教师行业协会做起,通过“政府-行业协会-教师”的结构性完善去整体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师德问题,以使教育伦理责任和义务通过广大教师身上来落在实处。 |
|
|
|